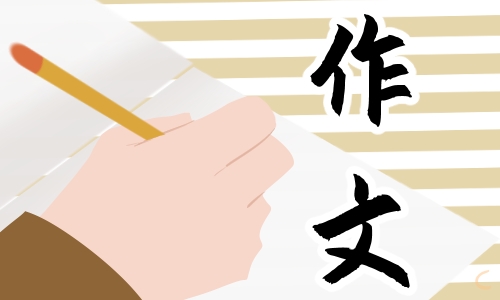【篇一:暖色的乡音】
我们这一代并非不懂方言,但说出口的往往是些夹生的方言,生硬而不自然。我以前也尝试过用土话与父母交流,却被他们戏称为“外国腔调”,几次之后只好作罢。
是啊,在如此重视标准普通话教育的今天,许多父母早就不愿一字一句地教给孩子乡音了——这种无益于学习成绩的事物,何必让其来占据孩子们的大脑空间呢?
可是,我仍然不愿这样一种看似可有可无之物逝去,只因脑海中的这样一些画面:我紧捏几块硬币,菜贩们将鲜翠水润的白菜铺在木板面上,我拣起几束交出硬币,菜贩皱纹横生的脸上绽开笑容,怜爱地用乡音说着“好孩子”;夕阳用瑰色笼罩白石板铺成的广场,几个稚童互相扑打追逐,笑声在空中荡起涟漪,忽然间旁边房屋上的一扇窗被推开了,一位母亲喊着“归吧(回家吧)”,那声音足以让所有客旅之人心弦震颤;我疾步走向那扇敞开的木门,外公将身影嵌入门框,一向寡言的他见到我便慈祥一笑:“梅,珍外(孩子,真乖)”,那画面突然美好得让人想落泪。我向来珍爱土话中“梅”的这个称呼,每当母亲这么唤我时,便感到言语和软亲切,诸般爱意,都在那一刻拥诸舌尖。这样的情感,在一板一眼的普通话中,是很难感受到的。
可是,这样的场景,逐渐也只能存在于回忆之中。母亲曾有次在外地偶遇青少年时的好友,两人惊喜而自然地用土话攀谈着,对方满脸疲惫的脸上也终于现出光彩。母亲又指指身边的小男孩,询问道:“你儿子会说咱们的方言么?”对方微叹了口气:“哪里会呢?他从小在外地长大,他爸爸也不是我同乡,平时交谈都是用普通话。”接着她又开始和母亲讨论起大城市孩子外语学习的紧迫,压力之大,自己孩子有多。
我站在一旁,茫然地想着,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会迁往外地,到时候,乡音是否真的还会有传承的可能?我猛然间心头一紧,几乎疼痛得不敢再想象它未来的宿命。
对更好未来的向往推挤着一代代青年涌向大都市,走向崭新的天地。外界的荆棘磨砺着年轻的身躯,逼着他们丢弃怀中一件件过去所恋之物。许多人开始回望归途,却又发现自己早已被羁绊在原地。
曾有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父亲与司机闲聊,问其是哪里人。司机说:“衢州,江山。”他又想了想,自嘲似地笑了,“小地方。你们应该没听过。”父亲大笑,用方言道:“哪个乡的?”司机反应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那一刹,鼻翼微张,整个面部都骤然柔软下来,嘴角放松地上扬,眼中映着车玻璃外距自己无比遥远的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他使劲动了动喉结,却很难说出话来。
我倚在后座的黑暗中,望着他脸上各种情绪的涌动,读着陌生人的故事,看到他心中的坚冰在父亲的那句乡音里融化成阳春三月里一弯和暖的山泉。
就像鲁迅心心念念的家乡的芸豆一样,乡音其实也不像记忆中那样动听。只是见到这些与故乡息息相关之物,脑中便会浮起父母的笑容,阡陌的芳香,烟火的温暖。无数回忆都盘纾于其间。身处荒漠般的大都市,见到这些记忆载体的一刻,万般柔情,涌上心头。
【篇二:暖色的乡音】
从遥远厚重的历史走来,向繁荣绮丽的未来奔去,我们的祖国有着数不清的文化印记。我们国家所提倡的匠人精神、节庆风俗、古村行走中所发掘出的地名故事、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无一不在彰显着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古国的灿烂文化。但对我而言,最难忘的是那淳朴的方言,最刻骨铭心的乡音记忆。
闽南语,起源于黄河、洛水流域,在时期、唐朝、北宋迁移至福建南部,发祥于泉州。而泉州则在闽南语的滋润下焕发着蓬勃生机。闽南语在“中国十大最难懂方言”中列居第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语言实际为中国方言的十多种语言之一。对于闽南人来说,这是莫大的骄傲与自豪。方言不仅是文化印记,更是一方人的声音记忆。
而我的声音记忆更多的存在于儿时。南音、北管、戏、高甲戏,在我的小时候都极受欢迎。节日的时候,总是全村人坐在戏台前,欣赏闽南语戏剧的魅力,整个乡镇的夜晚都笼罩在闽南语戏剧的古朴韵味之中,委婉缠绵,悠长典雅。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方言似乎渐渐地失去了它原有的辉煌。这样的乡镇戏剧演出越来越少,农村里的人也更多的走向城市,看的人少了,演的人也不多了。但我永远无法忘怀,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春秋》时的笑脸。就算方言的光彩逐渐暗淡,但这样的声音与唱腔,却始终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成为属于他们的不可磨灭的声音记忆。闽南语戏剧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戏剧,也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更多的是融在血液里的生活的一部分,是真正的母语,是真正的声音记忆。
很多年轻人走向城市,当他们在陌生的城市扎根时,午夜梦回,也会因为魂牵梦绕的乡音而泪湿耳畔吧。当他们的孩子,在接受城市教育后,而丧失方言的学习能力,他们也会忍不住沮丧吧。方言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记忆,更是浓浓的乡愁。会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传承与发展的人也就越来越少,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母语在岁月长河中消失殆尽吗?不!这绝不会是我们所想看到的。我们不想看到丰富多彩的方言戏剧就此失传,我们也不想看到方言文化无人继承,不想看到祖孙相见却因为语言不通而相对无言,更不想面对鬓毛未衰乡音已改的悲凉。
保护方言的行动迫在眉睫,这要赖于政府和学校的双向配合。政府应当进行对保护方言的宣传,在城市开设社区方言教学,让市民多进行方言文化的交流,让方言走向城市。学校应该开展方言教学课程,增设方言兴趣班等,只有下一代学会了方言,才能传承与发展。
希望乡音对我们而言不再只是声音记忆,不再只存在于梦里,而是切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用于人们的交流。希望乡音不失其重,不改其真。
【篇三:暖色的乡音】
像那冬天里的野姜花,每一丝花瓣都是一脉甘甜;像那戈壁中的小溪,每一滴水珠都是一分感动;像那海面上的大雁,每一块痕记就是一段情缘。——题记
浮霞轻烟,缠绕岸边的绿柳,穿越洁白的石桥,漫过小巷中古老的岩井,飘散到远处翠浪阵阵的麦田,栖息在青山里久远的草地上,摇曳起挂满紫藤的秋千,来回荡着荡着。它的每一个足迹都在诉说乡音的美丽,每一次结束就是一页醉人的故事,乡音角落便从这里开始……
你看那神秘而又沧桑的东西塔静谧在开元寺中,任岁月流逝,世事沧桑。每一个来访者必定要来拜谒这两座古塔。黑色的瓦片,褐色的木头,门紧锁着,所有的故事看似隔绝了,却仍然鲜活流转于人们的心里。古塔的精深与博大是人民用血汗铸成的灵魂,每一块砖石都烙刻着刺桐城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尽心守护祖先的心血,在那隐现辉煌的角落里,聚集了人类的欢声笑语,化作乡音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此去经年,当一朝一夕苍白的埋葬,都无法掩盖来去自如秉戾的思想,只有安溪的青茶可以禁锢万年的爱恋。一叶叶细小的茶叶,宛如姑娘们纤长的小手,五指间还残留思念的香味。从远处望,田田的茶叶,独自在微风中泛浪,每到采茶的季节,就可以闻到清冽的茶香。看一片片茶叶在煮茶人手中来回波动,一盅盅的香茶在姑娘们的曼妙手势中,莹盈芬芳。淡淡的清香同轻烟飞越红尘,如诉如歌。乡音的又一处角落就是这里,朴实无华,在三月的枝头开出酝酿千年的归期,一如翠绿的誓言。
当你来到这里,最当接触得便是乡音中最留恋的流水,一叶长长的小舟加上一双粗老的双桨,在晋江的水面上随风游弋,你就会感受到这水的幽柔,这水的清澈,这水的绵长。阳光穿越了纤尘,微雨润泽而下,千古以来这一腔守护之情涓涓流淌,从未断绝。这里的水从不结冰,因为儿女们赋予他们无限的温情,就连崇武古城的小鸟都舍不得远离,悠然拍动双翼,轻点水波,翩然徐徐。那里是烦心懊恼时身心休憩的角落,那里蕴涵着无数个生命的奇迹,上天赋予人间的生命渊源。
让阳光渗透所有的语言,让雨露滋润乡音的每一个角落。乡音,似飘散的轻烟,纱蓝的光泽,就像薄雾萦绕在泉州的每一个角落。
【篇四:暖色的乡音】
苍茫无边的夜色中,我陷入令人心悸的黑暗,每每梦回故乡,那最动听的声音,莫过于让我魂牵梦萦的摇篮曲与大河畔汹涌磅礴的交响乐。那一声声悠扬浩荡的汽笛声深深植入我的骨髓,在我的血液中无尽蔓延……
长大的我们痴迷于下课的钟声、电子音响中充满节奏感的摇滚声、KTV中放纵的歌声,但却没有一种声音能在你耳边久久回响,走进你美好而恬静的梦中。
小时候还不知事,像所有孩子一样,我躺在温暖的摇篮中,享受着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清闲时光,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担心,没有害怕。大人们在一旁说的什么,我不明白,也不曾记得,但唯独记住了耳畔久久回荡的歌声,似春风般温柔婉转,似花朵般柔软光滑。也许你要说这一定是母亲的歌声吧。其实不然,那是爷爷坐在我身旁时唱的歌,他放下他的刚毅、坚强,愿以如此温暖的声音伴我入眠,这是怎样一幅和谐美好的画面呀!有时,爷爷也会在我身旁干活,他卖力地做着手上的工作,不时会唱几曲号子,给自己鼓鼓劲儿。就这样,我往往禁不住困意,缓缓闭上沉重的双眼。
河畔的汽笛声不得不说也是家乡一大特色,我临河长大,爷爷奶奶家的田后就是通吕河,它奔流着,奔流着,从未止息。河旁的芦叶也随波飘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很喜欢河上轮船的马达声,并不震耳欲聋,但极富节奏。小时候没有电子产品,这一声声汽笛声在我耳中便成了难得的乐曲。我在汽笛声中醒来,又在汽笛声中睡去,伴着波浪撞击河岸的声音,我一天天长大,我离开过家乡,又回到了家乡,但却未忘记过故乡,是故乡的音伴我入睡,是故乡的情在我心中徘徊……
如今,交通日益发达便利,火车、飞机、地铁无处不通,故乡河里的轮船越来越少,我感叹于现在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为大大提升的生活条件而欢欣雀跃,却不知道这集爷爷的摇篮曲、大河旁游轮马达声于一体的乡音我还能再听见几回呢?
窗外阳光正好,一如爷爷的摇篮曲,柔和明媚,睁开眼,梦也该醒了,只是我上哪儿再去听这令我恋恋不忘的乡音呢……
【篇五:暖色的乡音】
此去经年,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思念,又与何人说?侧耳,却闻乡音一调,辗转顿挫,恍然隔世,一调乡音皆泯思寥。
这是我到长沙的第二年,对周边的街区早已熟门熟路,可于整个城市而言,还是如初来一般陌生。
每每出行,我总是靠在公交车的窗边在一排排琼楼玉宇寻找故乡的影子,当我对着那葱郁的大树发呆,回想着曾经的故事时,耳边响起的“长沙话”总会猛的将我拉回现实,原来,我早已离开了家乡。
长沙话是上挑着的,第一口气直直向上冲,中间的音总是刻意的被狠狠压下,转折的一声被拉长延伸,傲气十足。尾音像是一把钩子,挂住最后一声用力一提,提到尽处突然松开,任它直直下坠,化成一口浊气,消散于风中。
虽然在长沙生活,也能大概听懂长沙话,却总是学不会那一腔抑扬顿挫,当身边的人都操着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时,总会有一种排斥感将我笼罩,我不属于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乡。
当我沉浸孤独的思念之情中,我听到了一腔熟悉的音调……
“松他哒,快到咯”熟悉的乡音令我一震,蓦然回首,原来是一位老翁在与人打电话。他两鬓斑白,嘴角含笑,沙哑的嗓音说的是我的家乡话。我看着他,那声乡音让我仿佛回到了故时。榕树下,与外公外婆相处的点滴,永远敞开大门的街坊邻居,永远挂着微笑的糖糕店老板……过往的种种涌上心头,低头,发现已是泪眼朦胧。
那沙哑中带着一层亲切,第一个字第一声就是千回百转的,如浓浓的雾霭,轻柔温和,如迈过层层的青山,和缓地上扬,徐徐地下落,虽比不得吴侬软语有味道,确是质朴柔和的。
那一瞬间,我的灵魂像是被一只温和的手安抚着,所有的思绪都化为和煦的微风,所有的褶皱都被一一抹平。
流落异乡的游子最渴望的便是那一调属于故乡的独特方言。为什么中国人对“老乡”一词有着浓浓的眷恋,因为在异乡那一调属于家乡的话才显得弥足珍贵,如久旱逢甘霖,几抹乡愁早被那浓浓的乡音所安慰,便是冰冷陌生的城市也因此裹上了厚厚的家乡味。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街角路口涌动的人潮中一腔熟悉的乡音,惊喜的一声“老乡啊”寄去中国人最浓烈的感情,无论是天涯海角都不会孤单,一句乡情便可以温暖整座城。
【篇六:暖色的乡音】
我们这一代并非不懂方言,但说出口的往往是些夹生的方言,生硬而不自然。我以前也尝试过用土话与父母交流,却被他们戏称为“外国腔调”,几次之后只好作罢。
是啊,在如此重视标准普通话教育的今天,许多父母早就不愿一字一句地教给孩子乡音了——这种无益于学习成绩的事物,何必让其来占据孩子们的大脑空间呢?
可是,我仍然不愿这样一种看似可有可无之物逝去,只因脑海中的这样一些画面:我紧捏几块硬币,菜贩们将鲜翠水润的白菜铺在木板面上,我拣起几束交出硬币,菜贩皱纹横生的脸上绽开笑容,怜爱地用乡音说着“好孩子”;夕阳用瑰色笼罩白石板铺成的广场,几个稚童互相扑打追逐,笑声在空中荡起涟漪,忽然间旁边房屋上的一扇窗被推开了,一位母亲喊着“归吧(回家吧)”,那声音足以让所有客旅之人心弦震颤;我疾步走向那扇敞开的木门,外公将身影嵌入门框,一向寡言的他见到我便慈祥一笑:“梅,珍外(孩子,真乖)”,那画面突然美好得让人想落泪。我向来珍爱土话中“梅”的这个称呼,每当母亲这么唤我时,便感到言语和软亲切,诸般爱意,都在那一刻拥诸舌尖。这样的情感,在一板一眼的普通话中,是很难感受到的。
可是,这样的场景,逐渐也只能存在于回忆之中。母亲曾有次在外地偶遇青少年时的好友,两人惊喜而自然地用土话攀谈着,对方满脸疲惫的脸上也终于现出光彩。母亲又指指身边的小男孩,询问道:“你儿子会说咱们的方言么?”对方微叹了口气:“哪里会呢?他从小在外地长大,他爸爸也不是我同乡,平时交谈都是用普通话。”接着她又开始和母亲讨论起大城市孩子外语学习的紧迫,压力之大,自己孩子有多。
我站在一旁,茫然地想着,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会迁往外地,到时候,乡音是否真的还会有传承的可能?我猛然间心头一紧,几乎疼痛得不敢再想象它未来的宿命。
对更好未来的向往推挤着一代代青年涌向大都市,走向崭新的天地。外界的荆棘磨砺着年轻的身躯,逼着他们丢弃怀中一件件过去所恋之物。许多人开始回望归途,却又发现自己早已被羁绊在原地。
曾有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父亲与司机闲聊,问其是哪里人。司机说:“衢州,江山。”他又想了想,自嘲似地笑了,“小地方。你们应该没听过。”父亲大笑,用方言道:“哪个乡的?”司机反应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那一刹,鼻翼微张,整个面部都骤然柔软下来,嘴角放松地上扬,眼中映着车玻璃外距自己无比遥远的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他使劲动了动喉结,却很难说出话来。
我倚在后座的黑暗中,望着他脸上各种情绪的涌动,读着陌生人的故事,看到他心中的坚冰在父亲的那句乡音里融化成阳春三月里一弯和暖的山泉。
就像鲁迅心心念念的家乡的芸豆一样,乡音其实也不像记忆中那样动听。只是见到这些与故乡息息相关之物,脑中便会浮起父母的笑容,阡陌的芳香,烟火的温暖。无数回忆都盘纾于其间。身处荒漠般的大都市,见到这些记忆载体的一刻,万般柔情,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