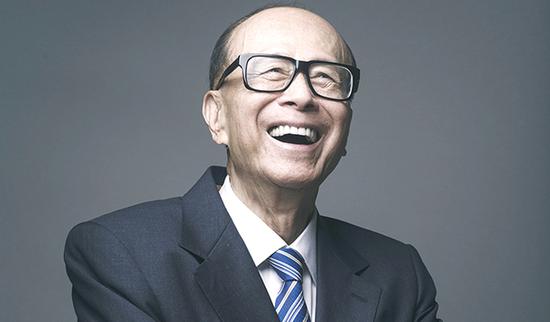儿时,最喜欢和一群小伙伴在自家菜园子玩耍。家人习惯把离家百十米远的那块地叫做“菜园子”,那是我心目中的一片“竹林”,也是我儿时的一座后花园。
我眼里真正的菜园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母亲喜欢在院子里种点时蔬。喜欢种葡萄的父亲,会精挑细选一些竹子,或整株或片开,或钻土或捆绑,在院子里搭起方便瓜果攀延的架子来。夏日里,母亲种的丝瓜和父亲种的葡萄,相约爬上竹架子,丝瓜藤和葡萄藤子恩恩爱爱地缠绕在一起。
勤俭持家的母亲,也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从院子里摘下的各种鲜嫩时蔬,满足自家需要后,她总是挨家挨户地去送给左邻右舍尝鲜,从不拿到家门口的菜市场去换钱。母亲目不识丁,说不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种文绉绉的话来。淳朴的她只是觉得帮助他人,总比占人便宜要踏实。
住在老街的那些年,街坊邻居都吃过父亲做的各种面食和母亲种的各种时蔬。
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这个面食魔术师善于把简单的面粉,变成各种可口的面食。馒头、花卷、水饺、酥角、面条、面疙瘩、油条、甜包子、菜包子、肉包子、千层饼……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父亲做不到。因为父亲各种花样面食,八口人的大家庭里从不会为吃什么而发愁。
成长路上,我们总是因为父亲那些与众不同的面食,常常忘了母亲也是一个烹饪高手。而她与父亲的神搭配,简直是天造地设。父亲善于做面食,母亲善于做饭。父亲善于煎炒,母亲善于煲汤。
作为土生土长的诏安人,我对粥有一份很深的情结。我知道这份情结,源于母親的巧手。母亲熬的粥,不稠。她总爱说,稀饭,就得稀一点。但她熬的粥从不会稀得惨淡。“稀而软糯,稀而浓香”,是母亲粥的特点,她把粥熬出了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夏天是院子里丝瓜疯长的季节。母亲做出来的丝瓜无论是炒还是煮汤,都是绿得可人。不会像别人家的一样带着惨不忍睹的暗黑。为了将丝瓜吃出新高度。除了日常的炒丝瓜,丝瓜蛋汤外,母亲还别出心裁地做起了丝瓜饭。一听到丝瓜饭,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黏糊糊的,粥不像粥,干饭不像干饭。但母亲做出来的丝瓜饭,跟平日里的干饭一样,粒粒分明,晶莹剔透,松软可口。还比平日里的白米饭多出了一份丝瓜的清香来。清甜软糯的丝瓜饭是儿时记忆里的人间顶级美味。
夏天也是苦瓜丰收的季节,当家人和邻居吃腻了苦瓜时,脑洞大开的母亲会把苦瓜洗净,切成小块状,放到烈日下暴晒一番,再找来洗净的罐子,将苦瓜干密封起来。
到了冬天,瓜果类的蔬菜变得稀罕起来。当家家户户终日只能唉声叹气地拿大白菜开涮时,母亲把封存的苦瓜干拿出来。在洗净的苦瓜干里放一小块肚肉,搁几只江鱼干或巴浪鱼干,煲一锅伴着肉香、鱼香和瓜香的苦瓜汤给我们喝。智慧的母亲冬行夏令,让我们在寒冬腊月里,幸福地吃上了反季节的蔬菜。
大方的母亲总是舍得给予,但习惯勤俭的她,却舍不得任何浪费和糟蹋。我想这也是她把时蔬种在自家院子里,把喂养家畜用的菜种在离家百十米的菜园子里的原因吧。
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在家的后院里养了不少家畜。为了让家畜吃饱喝足快快长大,母亲把离家百十米远的自家荒地,进行开垦拓荒。百平米的地皮,三分之一用来种植竹子,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种植家畜吃的菜。菜园子的外围再种三四棵苦枥子树。
我想我是懂母亲的。她不会把时蔬种在竹林边,是怕路人偷摘,怕顽童糟蹋。而猪食菜是没人会偷摘的,哪怕顽童摘下来玩玩后,扔到一边也不会影响家畜的食用。
母亲没有受过教育,估计也没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高贵情怀。她种竹子是因为竹子很实用。当我们体内火气太大时,她会摘些竹芯煮水给我们喝。家里晾衣服的竹篙,瓜果攀爬的架子,鸡舍,都是父亲从自家竹林里砍下来加工制作的。
那一片竹林成了我儿时的后花园。
春天里,我会和小伙伴在竹林的菜地里抓蚯蚓,比比谁抓的大,谁抓得多,然后再把他们放回菜地里,看看谁家的蚯蚓钻土钻得快。偶尔还会残忍地把蚯蚓切成两段,兴致勃勃地观察他们分别扭动的身躯,且美其名曰“助力繁衍后代”。
夏日里,我会在蝉鸣聒噪的午后,带上一本课外书,独自跑到竹林里。爬上那密密匝匝的竹丛中,倚靠在竹子上,享受着夏日的清凉和书的清香。竹子有很强的柔韧性,当我背上的这丛竹子歪得厉害时,会有另一丛竹子在旁边托付着,我尽管肆意地享受这份柔软的依托。
长大后,看电影《卧虎藏龙》竹林戏的打斗场面时,记忆里的那片清凉在瞬间被打开了。
当我躲在竹林里乘凉看书时,母亲也会和左邻右舍的几位大妈,一起坐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纳凉,喝喝下午茶,聊聊家长里短。清风经过巷子时,会顺手捎来不远处竹林的沙沙声。喝茶、聊天、听风,我想这应该是属于母亲的岁月静好了。
一个夏日的午后,穿着露趾凉鞋的我,约上一群小伙伴到竹林菜园子疯。不小心,左脚的大拇指被菜园里的玻璃划了一个口子。当时因为玩得欢,都没感觉到疼痛,直到脚上有湿湿的感觉,一看脚趾早已血流不止。小伙伴们看到我流那么多血,吓得四散奔逃。我也抱着必被母亲臭骂一顿的心,忐忑不安地回家。
心疼不已的母亲,根本顾不上骂我。她让我坐在石门槛上,找来黄药水和棉花,让父亲给我清洗伤口。伤口很大,母亲用“婴儿嘴巴大”来形容。接着,父亲用棉花和纱布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
忽地,母亲听到远远的有人叫她的声音。慌乱之下,她抓起旁边的一块硕大破布盖住了我流在地板上的那一滩鲜血。并让父亲快速地把我抱到里屋的床上,嘱咐我一定要忍住疼痛,不能吱声,更不能出来。
客人走后,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如此惊慌地将我藏起来。母亲叹了口气,微笑道:“小孩子玩的时候,磕磕碰碰受点伤,很正常。只是,你这次流了这么多血,看起来挺吓人的。如果让人家知道了,估计会破费一番,还是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
我的脚受伤以后,母亲每次去菜园子浇水摘菜时,总会留意园子里的各种碎玻璃、瓦片和小石子,任何会硌脚伤人的东西,都会被她清理掉。她用勤劳的双手在打理着我的后花园。
后来,父母将那个承载着我无限欢乐的菜园子赠送给亲戚建房子,分文不取。巧的是,受赠者就是我受伤那天来串门,母亲为了不给对方添麻烦,把我藏起来的那一位。再后来,母亲走了,父亲也走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脚趾上那个婴儿嘴巴大的伤口隐约还在。而母亲那句“还是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的教诲时常在我耳边萦绕着……
欢迎访问丛文库范文大全网!